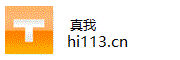当林言看到黄巢时,他惊讶的发现,当年打进长安的“冲天大将军”只能佝偻的坐在地上,双手无力的指了指,又迅速放下。 黄巢似乎也了解林言的来意,他以一种常人难以捉摸的眼神看向自己的亲外甥,那眼神中隐含着无奈。 “砍下我的头,换取你的富贵吧。” 这是唐末枭雄黄巢兵败虎狼谷后的一段辛酸往事,而黄巢也就是我们今天故事所要讲的主人公。那么,黄巢是谁呢? 他是农民军领袖,和王仙芝共举大业,也是落第书生,反诗“满城尽带黄金甲的”缔造者,在唐末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而他,也是少数屠杀数十万阿拉伯以及犹太商人的“食人魔”。那么实力强大的他,是如何走到穷途末路的呢?
落第书生曹州冤句,山东一隅,黄巢生于斯,长于斯。 在他少年时,黄巢的家族就学会钻朝廷的空子,以贩卖私盐为生,短短数十年,积累了丰厚的家底。 因此,即便在动乱不堪的唐末,黄巢也拥有难得的“教育”资本,绝不是底层人能够相提并论的。 可以说,他弓马骑射,不在话下,吟诗作赋,颇具才情。而黄巢的终极梦想,与现在的山东人类似,科举入仕。 正所谓:“周公子几代人的努力,凭什么输给你十年寒窗?”晚唐科场,没有公平正义可言,全是世家大族和人情世故的“宣扬点”。 故而,在黄巢怀着对未来的抱负,踏入考场时,遭遇的却是“意想不到”的落榜。 黄巢秉性孤高,常年的优越生活,养成了“自以为是”的性格,他无法接受失败,更不允许自己的理想,遭到打击。 于是,他写出了足以撼动后世的反诗: “待到秋来九月八,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,满城尽带黄金甲。” 可以想象,百花杀尽,黄金甲满城,字字如刀,黄巢的恨意直指长安,直指将他拒之门外的腐朽王朝。
然而,这也并非是黄巢个人的怒火。 安史之乱后,大唐的根基就已不复存在,藩镇割据四处蔓延,中央权威日渐衰微。 更致命的是,自唐懿宗末年,席卷全国的水旱灾害频繁“发生”。赤地千里,饿殍遍野,人间惨剧日日上演。 而这之中,造反最频繁的河南,灾难最为严重。 可高高在上的李唐宗室、官宦藩镇、世家贵族们,却选择“闭目塞听”。他们不仅不管不问,还抛出了“何不食肉糜”的“大唐版”:实在不行,可以吃树叶子。 似乎,每个王朝末期的统治者们都患上了同一种“病”,他们忘记了“水能载舟,也能覆舟”的古训,视底层为刍狗。 可当百姓活不下去的时候,陈胜、张角、窦建德,就随处可见了。
屠戮广州不久后,曾怀揣进士梦的“小镇做题家”黄巢,看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。他在老家冤句振臂一呼,聚众数千,加入到王仙芝的队伍中,起兵造反。 876年8月,黄巢、王仙芝横扫河南,十日连下八县。 事实上,在黄巢的指挥下,义军采用“游击”作战,避实击虚,驰骋江淮、河汉。反观前来“剿匪”的官军,顾此失彼,疲于奔命。 而此时的大唐王朝,遍地都是“干柴”。黄巢、王仙芝的义军转战四处,到处“暴兵”,队伍越滚越大。 短短半年,义军就膨胀到三十万人。 值得一提的是,若义军真如后世史书所描绘地那样嗜血残暴、四处屠城,可百姓却为何疯狂归附呢? 或许,在百姓眼中,坐视他们饿死的腐朽大唐,“残暴”更甚义军。当生路断绝,选择“拿生命当作赌注”,也是别无他法。 然而,纵观历朝历代末期,农民起义愈演愈大时,他们内部权力和道路的分歧就会成为分裂的“爆发点”。 当时,唐僖宗见义军势大,难以平定,就萌生了册封王仙芝为“左神策军押牙”的想法,意图招安。 王仙芝本就是“首鼠两端”之辈,他造反的目的,不是为了解救受苦受难的百姓,而是为了自己的前途。 因此,在唐僖宗向他“招手”时,他甩甩尾巴就去了。
然而,王仙之的“背叛”,让黄巢怒不可遏。他当众撕毁“招安”协议,痛殴王仙芝,带着自己的亲信,分道扬镳了。 不出意外,王仙芝的招安梦,也很快破灭,朝廷的许诺不过是调兵遣将的缓兵之计。 878年,“摇摆不定”的王仙芝,在黄梅遭遇曾元裕,兵败身死。而他麾下的残部,也不得不北走亳州,和黄巢会师。 直到此时,众人方才看清朝堂的“真面目”,他们迫切的推举黄巢为王,号“冲天大将军”,建元王霸,设官分职。 甚至,还喊出了“平均”的口号。 然而,经历了王仙芝“败亡”以及黄巢分家,义军的实力,大不如前了。可唐军却在曾元裕的指挥下,势如破竹,大有一口气吞掉义军的架势。 878年,黄巢也“招安”了。 可他却不是真“投降”,反而是无奈之举。为了缓解唐军围困,制造逃脱生天的机会,黄巢用自己的“名誉”,钓住了唐军。 在朝廷沉浸胜利的喜悦时,黄巢率人迅速越过江西,直进浙江。令人惊叹的是,他还能出其不意地攻陷重镇福建,兵指岭南,围困广州。 然而,兵临城下时,黄巢却未急着攻城,反而向朝廷开价,索求“天平军节度使”。 当时,宰相卢携断然拒绝,黄巢退而求其次,求任“安南都护、广州节度使”,却换来了羞辱性的“率府率”。 于是,黄巢兵发广州,一日就克,生擒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。
广州是唐朝重要的对外贸易窗口,在安史之乱时,唐廷曾向大食和波斯借兵平叛,因此大量的穆斯林、波斯商人涌入城中,经过百余年的发展,势力早已盘根错节。 阿拉伯商人苏莱曼说,他们曾趁乱劫掠过广州,前刺史韦正矩弃城而逃,使广州一度成为他们的“殖民地”。 然而,黄巢却不是韦正矩,对于不服从命令,且心怀野心又多金的商人,他毫不犹豫的挥起了手中的屠刀。 事实上,途径泉州时,黄巢已屠杀数万犹太商人。 在广州,他又进行了更为彻底的清洗,被屠杀者总数近二十万,仅穆斯林、基督徒、犹太人就高达十二万。 此次屠杀,彻底摧毁了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在华南经营数代的根基,也断绝了他们通过“钱财”夺取大唐国土的念想。 扫平南方后,黄巢的目光,再次投向了让他魂牵梦绕的长安。
身死虎狼谷880年,黄巢北伐势如破竹,潼关在义军的猛攻下土崩瓦解,长安门户大开。唐僖宗效仿先祖唐玄宗,仓皇逃离,奔向蜀地。 12月13日,黄巢走进大明宫,他正式登基称帝,国号“大齐”,建元“金统”。可他的皇位还没坐稳,长安就变成了“人间地狱”。 即便,黄巢虽下令“禁止军中乱杀”,但对富贵的渴望以及对权贵的仇恨,已扭曲了义军的纪律。 而与长安百姓相比,昔日高高在上的门阀士族,遭遇更为惨烈。他们被随意拖出府邸,肆意屠杀,劫掠。 可以说,黄巢入主长安后,秩序荡然无存,只有暴虐。 不过,黄巢的“好日子”也没过多久。唐军发起反攻后,黄巢不得不退出长安,将刚到手的帝都,拱手相让。 有趣的是,在黄巢和唐僖宗的极限拉扯中,“戏份”最多的却是长安百姓。 黄巢入主长安时,百姓以为要改天换地,迎接新生活了,就锣鼓喧天、夹道欢迎;可在唐军反攻时,百姓又欢天喜地的迎接离开长安不过数月的“牛夫人”。 然而,唐军进城后,却无缝衔接了黄巢大军的抢劫“事业”。
与此同时,蛰伏城外的黄巢,也暗中命令部将孟楷杀个回马枪。百姓们再次上街欢迎,可满载赃物、行动迟缓的唐军却成了屠杀对象。 长安,又落入黄巢之手。 只不过,对于“反复无常”的长安百姓,他再无“留恋”。史载,黄巢军对长安进行了无差别的大屠杀,死者高达八万余人。 整座长安城,尸横遍野,血流成河,人走在路上都得卷起裤脚,不然就淌着血水。 不久后,在诸镇联军的围攻下,黄巢焚毁宫室,弃城东逃。当他流窜至河南、山东时,却遭遇了罕见的饥荒。 在此绝境下,黄巢和他的部下,成了史书笔下的“超级食人魔”。 884年,在李克用和唐军的联合打击下,黄巢逃奔虎狼谷。 当时,64岁的黄巢已穷途末路,他要求外甥林言杀死自己,投降换取生路。林言照做了,还“贴心”地砍下了黄巢妻儿的脑袋,献给唐军。 然而,当林言兴高采烈的以为可以得到“高官厚禄”时,李克用非但没有饶恕他的罪行,反而将他杀了。 善恶到头终有报,一点不假。